这一日,终于搁下扇子。来自天上干燥清爽的风,吹得我一袂飞举,并从袖口和裤管口钻进来,把周身滑溜溜地抚动。我惊讶地看着阳光下的依旧夺目的风景,不明白数日前那个酷烈非常的夏天,突然跑到哪里去了。
是我逃遁似的一步跳出了夏天,还是它在一夜间崩溃?身居北方的人,最大的福分,便是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四季分明。我特别能理解一位新加坡朋友,每年冬天要到中国北方住上十天半个月,否则会一年里周身不适。好象不经过一次“冷处理”,他的身体就会发酵。他生在新加坡,祖籍河北;虽然人在“终年都是夏”的新加坡长大,血液里肯定还执着地流着大自然四季的节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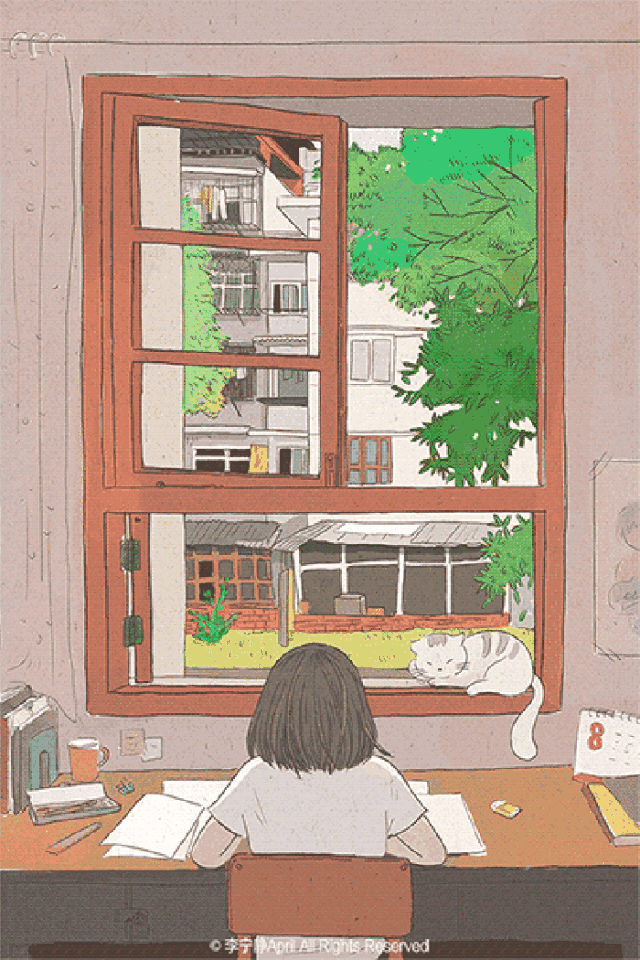
在每一个节拍里,大地的景观便自然的更替与更新。四季还赋予地球以诗意,悟性极强的中国人,在四言绝句中确立的法则是:起,承,转,合。这四个字恰恰是四季的本质。起始如春,承续似夏,转变若秋,合拢为冬。合在一起不正是地球生命完整的一轮?为此,天地间一切生命,全都依从这种节奏,无论岁岁枯荣与花草百虫,还是长命百岁的漫漫人生。在这生命的四季里,最壮美,最热烈的,不就是这长长的夏天么?
女人们孩提时的记忆散布在四季;男孩们的童年往事大多是在夏天里。我们儿时的伴侣总是各种各样的昆虫,蜻蜓、天牛、蚂蚱、螳螂、蝴蝶、蝉……此外还有青蛙和鱼儿。它们都是夏日生活的主角,每种昆虫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快乐,甚至我对家人和朋友们记忆最深刻的细节,也都与昆虫有关。比如,妹妹一见到壁虎就发出一种特别恐怖的尖叫。比如,邻家那个斜眼的男孩子专门捕捉蜻蜓,比如,同班一个最好看书的女生头上花形的发卡,总招来蝴蝶落在上面。再比如,父亲睡在铺了凉席的地板上,夜里翻身居然压死了一只蝎子。这不可思议的事使我感到父亲的无比强大……

在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般夏天的难耐与煎熬。唯有在此后艰难的人生中,才体会到“苦夏”的滋味。快乐把时光缩短,苦难把岁月拉长,一如着长的仿佛没有尽头的苦夏。我至今不喜欢谈自己往日的苦楚与磨砺。相反,我却从中领悟到“苦”字的分量。苦,原是生活中的蜜。人生的一切收获都压在这沉甸甸的苦字下面。然而,一半的苦字下面又是一无所有。你用尽平生的力气,最终获得与初始时的愿望去之千里。你该怎么想?
于是,我懂得了这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的折磨,而是人们顶着毒日头沉默又坚韧地苦斗,人生的力量全是对手给的,那就是,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强者之力最主要的是承受力,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也许为此,我的写作一大半是在夏季。

很多作家,包括普希金,不都是在爽朗而惬意的秋天里开花结果?我却每每进入炎热的夏季,反而写作力加倍的旺盛。我想,那一定是那些沉重的人生苦夏,锻造出我这个反常的性格习惯。我太熟悉那种写作久了,汗湿的胳膊粘在书桌的玻璃上,美妙无比的感觉。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友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枯涩与艰辛,甚至还有一点儿悲壮。友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它给你,而是你给它。
年年盛夏,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苦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信心十足。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夏天的最后一刻,总是它酷热的极致。我明白了,它是耗尽自己的一切,才显示出盛夏无边的威力。生命的快乐是能量淋漓尽致的发挥。谁能像盛夏用一种的形式,创造出这盛极而衰的瞬间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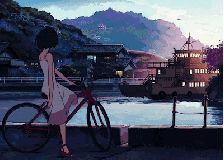
天气是热的,可是一早一晚相当的凉爽,还可以作事。会享受的人,屋里放上冰箱,院内搭起凉棚,他就会不受到暑气的侵袭。假若不愿在家,他可以到北海的莲塘里去划船,或在太庙与中山公园的老柏树下品茗或摆棋。“通俗”一点的,什刹海畔借着柳树支起的凉棚内,也可以爽适的吃半天茶,咂几块酸梅糕,或呷一碗八宝荷叶粥。愿意洒脱一点的,可以拿上钓竿,到积水滩或高亮桥的西边,在河边的古柳下,作半日的垂钓。

太阳落山在夏季是那么艰难,但它毕竟是要落山的,放暑假的孩子关注太阳的动静,只是为了不失时机地早早跳到护城河里,享受夏季赐予的最大的快乐。
黄昏时分驶过河面的各类船只小心谨慎,因为在这种时候整个城市的码头、房顶、窗户和门洞里,都有可能有个男孩大叫一声,纵身跳进河水中,他们甚至要小心河面上漂浮的那些西瓜皮,因为有的西瓜皮是在河中游泳的孩子的泳帽,那些讨厌的孩子,他们头顶着半个西瓜皮,去抓来往船只的锚链,他们玩水还很爱惜力气,他们要求船家把他们带到河的上游或者下游去。于是站在石埠上洗涮的母亲看到了他们最担心的情景,他们的孩子手抓船锚,跟着驳船在河面上乘风破浪,一会儿就看不见了,母亲们喊破了嗓子,又有什么用?
夜晚来临,人们把街道当成了露天的食堂,许多人家把晚餐的桌子搬到了街边,大人孩子坐在街上,嘴里塞满了食物,看着晚归的人们骑着自行车从自己身边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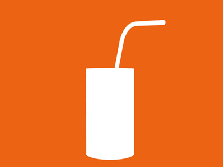
什刹海会贤堂的名件“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食客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信远斋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酽。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纯醪,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信远斋,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尽七碗方始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信远斋的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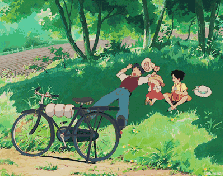
第一年夏天,我没有读书;我种豆。不,我比干这个还好。有时候,我不能把眼前的美好的时间牺牲在任何工作中,无论是脑的或手的工作。我爱给我的生命留有更多余地。有时候,在一个夏天的早晨里,照常洗过澡之后,我坐在阳光下的门前,从日出坐到正午,坐在松树,山核桃树和黄栌树中间,在没有打扰的寂寞与宁静之中,凝神沉思,那时鸟雀在四周唱歌,或默不作声地疾飞而过我的屋子,直到太阳照上我的西窗,或者远处公路上传来一些旅行者的车辆的辚辚声,提醒我时间的流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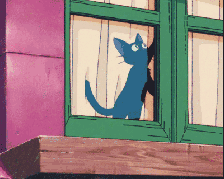
加勒比地区的人有一种迷信,以为打开门窗可以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凉爽引至屋内。在这里出生并长大的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妻子,起初也曾因门窗紧闭而感到压抑,但最终,他们还是采纳了罗马人抵御炎热的绝妙法子,即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八月紧闭门窗,不让街上炽热的空气钻进来,等到了晚上再全部敞开,让凉风入户。从那时起,他们家便成了拉曼加区炎炎烈日下最为凉爽的处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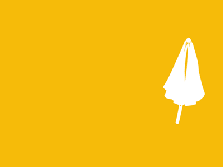
每天上午十一点钟光景,一列火车穿过广袤的香蕉种植园,准时抵达镇上。人们日后一定会记得,那是一列颜色发黄、沾满尘土、裹在一片令人窒息的烟雾之中的火车。紧挨着铁路,满载着一串串青香蕉的牛车在尘土飞扬的小道上缓慢地行进。气候炎热潮湿。火车抵镇时,酷热难当,在车站等候的妇女们一个个都打开色彩缤纷的阳伞以抵御炎日的炙烤。

时间已过正午,天气酷热。酒吧里到处都是河面反射过来的阳光,金光闪闪。啤酒很淡,但足以让我们昏昏欲睡。
此刻正是午后不久,阳光炽烈,一切都像着了火似的,这火烧得正旺,但也微微显出逐渐柔和下来的态势。河上波光荡漾,浑浊的河水由黄色转为白色和金色。河上到处都是装有舷外发动机的独木舟,汽船开进开出的日子向来如此。独木舟上有各自所属“机构”的名称,都是一些大而无当的名称,用大大的字母漆在舟身两侧。有时候,独木舟从一片波光中穿过,在强光下,舟上的乘客都成了剪影。此时看过去,他们都坐得低低的,只能看出肩膀和圆圆的脑袋,就如同卡通画上的滑稽人物,正在进行一趟荒诞不经的旅行。

风吹痛了苔丝的白纱衣裳,一直吹到她的皮肉儿。她刚洗过的头发,也被披散在背后。她拿定了主意。不露出害怕的样子来,但是她却用手抓住了德伯握缰绳的那只手的胳膊。
太阳透过榆树的密密层层的叶子,把阳光的圆影照射在地上。夏末秋初的南风刮来了新的麦子的香气和蒿草的气息。北满的夏末初秋是漂亮的季节,这是全年最好的日子。天气不凉,也不顶热,地里还有些青色,人也不太忙。

当年,我们这些孩子幻想着能用常年积雪在酷暑的街道上打雪仗。天热得令人难以置信,午睡时尤甚。大人们总是抱怨,仿佛高温在每天都是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自出生以来,我总听到有人不知疲倦地唠叨,说铁轨是夜里铺的,联合果品公司的房子也是夜里建的,因为白天晒得滚烫的工具根本没法儿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