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书出得很多,可真叫人看一眼就喜欢,愿把它放在自己的书架上随时欣赏把玩的却极少。


北大中文系无论什么样的课程,几乎每个老师都会提到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位老师,他们是文学史家们口中的“燕园三剑客”。
为了编这几本小书,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位教授暑天闷在10平方米的小屋内,拟提纲、分专题、选文章;泡图书馆,翻旧期刊……有时三人居然会“大动干戈”,争得脸红耳赤。陈平原老师后来自嘲,当时实在不够洒脱。
我们不靠它赚名声,也不靠它发财。只希望有一套文章好读、装帧好看的小书,可以送朋友,也可以搁在书架上。
如今书出得很多,可真叫人看一眼就喜欢,愿把它放在自己的书架上随时欣赏把玩的却极少。
有人说,中国的好文章还不是遍地黄金,大批名家名作,随便选选都可称作名家荟萃?
漫说文化丛书所选文章从章太炎、梁启超到汪曾祺、贾平凹,汇集了97位近现代名家之作,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

你会发现,选文淘汰了不少徒有虚名的“名作”,所选更多是有文化意味又妙趣横生的文章。
丛书所选文章既有文化意味而又妙趣横生,让我们感受到“文化”不仅凝聚在高文典册上,而且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落实为我们所熟悉的一种情感,一种心态,一种习俗,一种生活方式……

读书、买书、藏书,这无疑是古今中外读书人共有的雅事。正因为其乐无穷,才引得一代代读书人如痴如醉。
在《读书读书》中,林语堂教你怎么读书,“兴味到时,拿起书本来就读。”(《读书的艺术》)
老舍则教你读什么书:“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放下,不客气”(《读书》)
叶灵凤会与你分享书斋里的趣味:“在这冬季的深夜,放下了窗帘,封了炉火,在沉静的灯光下,靠在椅上翻着白天买来的新书的心情,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搜寻着新的伴侣。”(叶灵凤《书斋趣味》)

蔡元培先生的《夫妇公约》中表现的“超前意识”与其文体的陈旧一样令人吃惊。
聂绀弩在女权问题上倾注了最大的战斗激情;徐志摩则作了出自中国浪漫主义男性诗人的阐释和理解。
郁达夫、何其芳、陆蠡、孙犁……他们或谈初恋,或寄哀思,或忆旧情,至性至情。
文体、语言、观念、思想,无不在时空的流动中嬗变、分化、冲突,极为生动,十分有意思。不信,请君开卷,细细读来。

正如徐志摩所说,人伦之情是人生里最基本的事实,最单纯的,最普遍的,最平庸的,最近人情的经验。
周作人说:“世上太多的大人虽然都亲自做过小孩子,却早失去了‘赤子之心’,好像‘毛毛虫’的变了蝴蝶,前后完全是两种情状,这是很不幸的”。
收入本集的描写儿女情态、童趣盎然的作品,不仅是表现了真挚的亲子之爱,而且有着相当深广的历史、文化的内涵。

有人说,中国这个民族不长于思辨,艺术想象力也不发达,却最懂世故人情,这大概是有道理的。
这类话题,于人生阅历之外,往往透着几分智慧,闲谈絮语中的智慧、风趣,连同那轻松自如的心态,在“玩世不恭”的调侃语调底下内蕴着几分愤激与执著。
读这样的散文,不管作者怎样放冷箭,说俏皮话,你都能触摸到那颗热烈的心,感受着那股“叫真”劲儿,这也是构成了本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学的时代“个性”的。

关于闲情,中国古代文人早有领悟,从陶渊明、苏东坡,到张潮、李笠翁,都是“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的“快乐天才”。
林语堂为洋派的抽烟卷辩护;夏丏尊怀疑“中国民族是否都从饿鬼道投胎而来”,因此才如此善吃;丰子恺讥笑中国人是吃瓜子的天才;
林语堂称西装令美者更美丑者更丑;梁实秋谈男子服装千篇一律,而女子的衣裳则颇多个人的差异;
周作人喝清茶,丰子恺品黄酒,贾平凹觅食小吃,实在都说不上糜费,可享受者所获得的乐趣与情致,确又非常人所能领悟。
郁达夫要求的住所是能登高望远,房子周围要有树木草地;梁实秋欣赏不能蔽风雨的“雅舍”,则因其地势偏高得月较先,虽说陈设简朴但有个性,“有个性就可爱”。
若一个人的生活中没这些小情趣,当然也能活下去,可生活之干燥粗鄙与精美雅致的区别,正在这“无用的装点”上。
作为现代人,我们更要培养一个易感的心境以及一双善于审美的眼睛,“努力的工作,尽情的欢乐”,把握好“忙”与“闲”之间的比例,人生的精义就在于这个颇为微妙的“度”。

“乡风”与“市声”,古老的农业文明的旧中国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新中国之间的历史大决战,它们的消长起伏,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许多现代中国作家都自称“乡下人”:沈从文、芦焚、李广田……作家们的生活方式、心理素质、审美情趣不同程度的“乡土化”,无以摆脱的“恋土”情结,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面貌。
老舍在北京捕捉到的,是“象小儿安睡在摇篮”里的温暖,安稳,舒适的“家”的感觉;郁达夫在扬州古城苦苦追寻而终不可得的也是那一点田园的诗意,他觉得这里“荒凉得连感慨都教人抒发不出”……
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人多是‘生命之川’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人”在生命的流动中,本能地就一边“向前”,一边“反顾”吧。

在这本《说东道西》里,作家们众“说”纷纭,他们以那样平和的语调,洒脱的态度,对各民族(自然包括本民族)文化的优劣得失,作自由无羁的评说,最引人注目的是,前辈人在说“东”道“西”时所显示的平等、独立意识。
你会发现,许多作者在说“东”道“西”时,宇里行间常充满了幽默感。他们带着“世界民”的眼光和胸襟,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去考察“东”“西”文化。“东”“西”文化在互为参照之下,都同时显示出自身的谬误与独特价值,这既“可笑”又“可爱”的两个侧面,极大地刺激了作家们的幽默感,这样的“幽默”,丰厚而不轻飘,既耐品味,又引人深思。

人类最难摆脱的诱惑,或许就是生的欲望和死的冥想。而这两者又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谈生不忘说死,说死就是谈生。
人生一世,当然不只是鉴赏他人和自己的生生死死,更不是消极地等待死神的来临。就像唐弢笔下那死亡之国里不屈的灵魂,“我不怕死”,可我更“执着于生”;只要生命之神“还得继续给予人类以生命”,“我要执着于生”(《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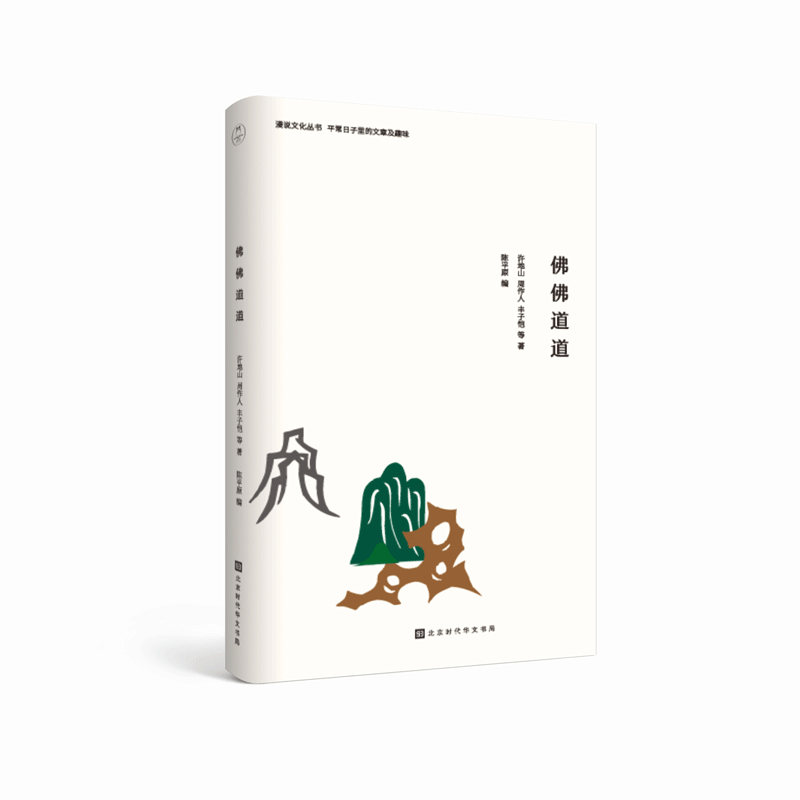
许地山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佛家的根本精神“慈悲”:“我愿你作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愿》)
苏曼殊的不僧不俗亦僧亦俗至今仍为人所称羡,不只是其浪漫天性,其诗才,更因其对宗教的特殊理解。
至于龙师父这样“剃光头皮的俗人”,一经鲁迅描述,也并不恶俗,反因其富有人情味而显得有点可爱(《我的第一个师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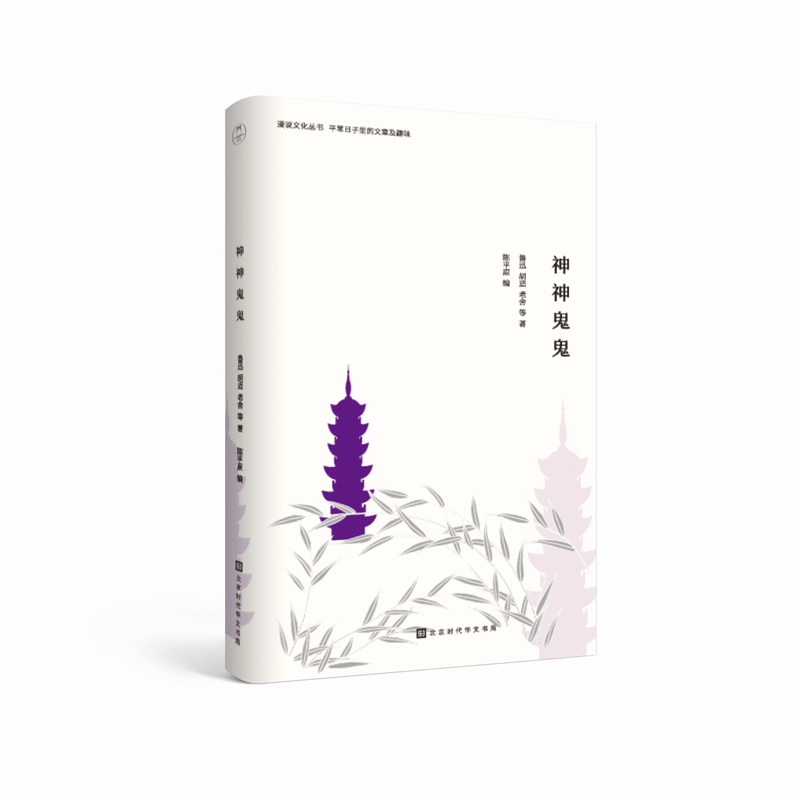
其实,鬼神之说挺有诗意,“有了鬼,宇宙才神秘而富有意义”(许钦文《美丽的吊死鬼》)。
李金发慨叹:“那儿童时代听起鬼故事来,又惊又爱的心情!已不可复得了,何等可惜啊!”(《鬼话连篇》)之所以“不可复得”,因为接受了现代科学,不再相信神鬼。
中国现代作家中无意于苍生者实在太少,故不免常常借鬼神谈苍生。鲁迅笔下“发一声反狱的绝叫”的地狱里的鬼魂(《失掉的好地狱》),老舍笔下无处无时不令人讨厌的“不知死的鬼”(《鬼与狐》),周作人笔下“附在许多活人身上的野兽与死鬼”(《我们的敌人》),还有李伯元笔下的色鬼、赌鬼、酒鬼、鸦片烟鬼(《说鬼》),何尝不是都指向这“清平世界朗朗乾坤”?
漫说文化丛书所涉及作者近百位,尚在版权期内的超过50位,为保证版本的合法与权威性,尊重每一位作者,编辑团队辗转联络到众多作者及其后人,版权代理,全书所有尚在版权期内的文章,一一获得版权所有人的亲笔授权。这是对文字的敬畏,也是对作者、对文化的尊敬。

某种意义上,科技正在改变国人的阅读习惯,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听书”成了时尚。

无论是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还是周作人的“有雅致的白话文”,抑或叶圣陶的主张“作文”如“写话”,都是强调文字与声音的紧密联系。
这些文章既“上口”,又“入耳”,兼及声调和神气,这样的好文章,在“漫说文化丛书”中比比皆是。

做饭的时候听听夏丏尊《谈吃》,听听贾平凹讲《陕西小吃小识录》,顿时食欲猛增,你要考虑是不是再多加几个菜了。
跑步的时候听听王力的《蹓跶》,夏丏尊《幽默的叫卖声》,仿佛走进了另一个时空,连路边的风景都赏心悦目起来了。
晚上睡觉时听听老舍的《小动物们》,俞平伯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在朦胧的夜色里沉沉地睡去,做的都是温柔的梦。
漫说文化丛书采用双封设计,特种纸护封,淡雅米色,蓬松度高,触感温润;封面元素采用印银、多种专色交叉印刷工艺,色泽鲜艳饱满;内文排版考究,舒阔,阅读体验极佳;32K开,成品尺寸147×210,方便携带。


几乎每个喜欢读书的人都痴迷“藏书票”这种“东西”,读书确实应该是一种更高级的精神享受。
一提到藏书票,就不得不想到崔文川先生,有不少爱书家将他称为“藏书票文化的传播者”。崔文川痴迷藏书票,常年浸淫此中,使得他设计的藏书票极富艺术魅力。
由他亲自操刀,为这套“漫说文化丛书”设计的这套藏书票,跟随书的主题,每题1张,共10张,每一款都别具匠心。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