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据台湾媒体报道,著名作家林清玄过世,享年65岁。林清玄的散文集不仅曾是台湾图书畅销榜的第一名,在大陆也有很高的销量,仅2013年4月出版的《林清玄散文精选》,发行册数就有约99.6万册。林清玄也和余光中、余秋雨、毕淑敏等人一道,是中学课文的常客。
说这几位散文家影响了一代青年的成长,并不夸张。是什么特质让林清玄的散文可以在大陆畅销不绝?无法对更严肃、深入的问题继续追问,而总是满足于《瓦尔登湖》或《金刚经》似的道理拷贝,是否在成就了林清玄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文学成就?


昨晚微信群里就传出他去世的消息,媒体人、出版人求证信源,手快的新媒体编辑已备好稿子,但几个小时后,没有回音,以为是谣言,没想到今天被证实。
林清玄先生的散文,我中学时读过很多,《在云上》《清音五弦》《心的菩提》《情的菩提》《马尾》《林寺》等,报刊亭里,《读者》《青年文摘》《意林》这些杂志很喜欢选他的文章,课文里也有,具体篇目记不清了,只记得读他的散文,就像月下闲逛人工园林,有清淡之气,也有雕琢之感,所叙所写,往往是一些有哲理、禅意的小事,传达些许人生的道理。
记得那时候,他的散文是学作文的素材,中学里有很多小林清玄,字里行间有一股装模作样的禅意,当时同学模仿的对象,还有汪曾祺、周国平、毕淑敏、余秋雨、冰心等,爱借鉴的书,则可以追溯到《小窗幽记》《菜根谭》。
大学后不怎么读林清玄了,因为他的散文已不能解答我的困惑。较之鲁迅,问题意识不够深刻,林清玄本身也不是用文章锥心刺骨的人。较之周作人、汪曾祺、林语堂,他的散文也不够隽永。许是因为林清玄太想传达他的道理,有时急切了些,而雕琢感尤在,反而有损文章的质地。
不过,我依然庆幸中学时期读林清玄的日子。他去政治污染的文字、一点点生活的诗意,让我在作文八股和大鸣大放的抒情之外,看到了一种别样的文章之美。而现在,当林清玄去世,我想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的散文能在大陆畅销不绝?哪怕是在对纯文学冲击巨大的新媒体时代,仍然流行。
他的散文集不仅曾是台湾图书畅销榜第一(《身心安顿》《烦恼平息》在台湾创下150版的热卖记录,《打开心灵的门窗》一书创下高达5亿元台币的热卖记录),在大陆也有很高销量,根据《出版商务周报》公布的数据,2013年4月出的《林清玄散文精选》,发行册数就有约99.6万册。作家出版社也透露,《气清景明,繁花盛开》曾加印18次,《人间有味是清欢》曾加印14次,销售量均超过20万册,《林清玄菩提十书》《林清玄经典散文系列》也频频加印,有很好的市场反响。而在中学课文上,林清玄也和余光中、余秋雨、毕淑敏等人一道,是文章的常客。说这几位散文家影响了一代青年的成长,并不夸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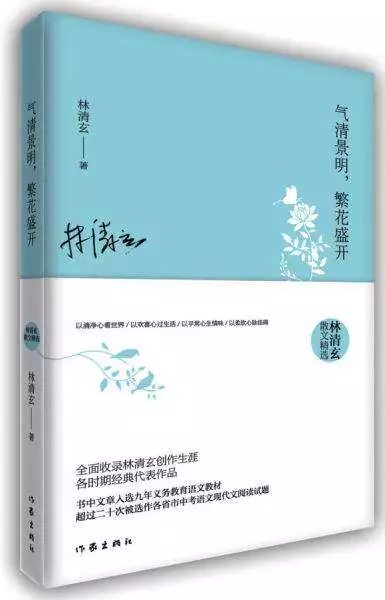
他的文字对大众是敞开的,没有学院派刻意建造的壁垒,也没有智识的卖弄,他的散文很少用生僻字、长句,用的典故也多耳熟能详,这一点和周作人、钱锺书就很不同。
周作人虽然散文造诣很高,但他古朴甚至有些文言的遣词造句,还有大量的引经据典,使得大众敬而远之。他最为大众熟悉的散文,比如《北平的秋天》,恰是引经据典最节制,文风也较为白话的,而《风雨谈》《永日集》《药堂杂文》等,就因为难读而远离大众。
众所周知,钱锺书更是一位引经据典的高手,他的书袋和他的比喻一样密实,而他并不以此为卖弄,实在是因为他的求学路径所致。他在学问上继承了乾嘉学派,去英国留学,又习得绅士小品文的技法,融会贯通,自成一路,由此给予读者智性的愉悦,但客观上,对读者也提出很高的要求。
相比之下,读林清玄的散文就不必大费周章,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市井小民,都能很快读进去林清玄的文章,一是生活化;二是对智性没有太高要求;第三,林清玄对节奏的把握很好,即便在新媒体时代,他的文章也能流行。
而且,尽管林清玄所处的地标对大陆读者别有一番滋味,但他巧妙地避开了政治的光谱,几乎是在虚无政治中建筑自己的美学。林清玄最被大陆读者知晓的散文,如《身心安顿》《烦恼平息》《温一壶月光下酒》、《白雪少年》《在梦的远方》《红心番薯》《光之四书》等,尽皆关于平凡生活,而远离政治。当龙应台在《野火集》烧起自己的原野,林清玄则潜心佛法,在修行中缓解生活的焦虑。彻底从敏感议题中抽身,书写老少皆宜的画面,让出版商引入林清玄作品消去顾虑,教育者们也可以大大方方地向学生朗读林清玄的散文,有了课文的推广,加之林氏散文本身的趣味,八九十年代,林清玄如同一道春风吹入千万寻常百姓家。

但这还不是林清玄流行的关键原因。生活化、节奏感都只是工序,真正将林氏散文捧进千家万户的原因,是他切中了都市中产和预备中产的口味,在字里行间灵活地演绎中产美学。
这种美学的要诀,在于营造出一个去焦虑的审美乌托邦,精致地勾勒出一幅岁月静好的图景,在山水明月与佛意参禅中,小心翼翼地呵护现代人的内心安定,从而在一点点意境和审美的愉悦中,消解他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尽管实际上,林清玄的散文并不能化解问题,也不具备化解的职能,但在消费演进的过程中,他的散文已经化作一张精致的屏风,成为中产生活的点缀。这些目标读者以谈论林清玄为趣味,以追求体面的人生作为自己的精神指向,至于时代的具体问题究竟如何、我们身边或者远方的残酷,他们也许会怜悯,但绝不会深入,那会令他们不安,也会打破他们的体面,与其如此,不如退居自己的精神田园,用种种精致、休闲之物填充需要慰藉之处,过上所谓优雅的生活。
其实,不只是林清玄,蒋勋、木心、毕淑敏、汪曾祺等散文家的长销,乃至时下流行的灵修、西藏游、新乡村实验等,都能从这一层心理中找到原因。而缺乏真正的精神指引,只能用体面和优雅打扮人生,在实际上经不起的推敲或已然陈词滥调的哲理中得到慰藉,也不只是中产阶级的困局。麻痹灵魂、远离深刻,确乎已成为时代潮流。
当然,指出这一点,并非苛责追求散文生活化、诗意化的散文家们,市场选择了谁,并不由作者自身决定,而解决现代人精神危机这个上下求索都未必能得到答案的问题,交给林清玄等散文家,更是强人所难。
然而,无法对更严肃、深入的问题继续追问,总是满足于《瓦尔登湖》或《金刚经》似的道理拷贝,在成就了林清玄的同时,也限制了他的文学成就。除了那并不深刻的玄思和逃避真正问题的悠闲之外,读者无法从林氏散文里获得更多,他能让人感到舒适,但舒适本身就是可疑的。

“‘清欢’是什么呢?清欢几乎是难以翻译的,可以说是‘清淡的欢愉’,这种清淡的欢愉不是来自别处,正是来自对平静的疏淡的简朴的生活的一种热爱。当一个人可以品味山野菜的清香胜过了山珍海味,或者一个人在路边的石头里看出比钻石更引人的滋味,或者一个人听林间鸟鸣的声音感受到比提笼遛鸟更感动,或者甚至于体会了静静品一壶乌龙茶比起在喧闹的晚宴中更能清洗心灵……这些都是清欢。”
我这种“清淡的欢愉”也是林清玄在散文上的追求。而他自己可能也想不到,这种清欢或谓之佛系清雅的趣味,十分合乎文革结束后的文学潮流。
改革开放后,散文界兴起了一股去宏大美学的潮流。反思宏大、雄浑的美学,提倡生活化、诗意化的美学,沈从文、汪曾祺、毕淑敏、冯骥才乃至民国的周作人等,他们的作品得以焕发第二春。这种风潮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写作者,曹文轩后来评论汪曾祺时就回忆道:“有见识的读者和评论者,都有一种惊奇,觉得总在作深沉、痛苦状的文坛忽地有了一股清新而柔和的风气。”
今天的读者已经很难理解当时大众对清新文学的渴望,如果没有十年文革对文学趣味的压抑,六七十年代“雄浑”文风对文坛的桎梏,清新文学也就不会在隐忍多年后,于八十年代爆发出它的生命力。这种清新文学就站在雄浑文学的对立面,高度去政治化、个体化,主张回归到平凡的生活和乡土之中,注重内心的修行,它们文辞清雅、风格闲适,所叙之事多是花鸟虫鱼或底层人物,所抒之情多与佛道并行,这里没有革命也没有英雄,有的只是对回归宁静的向往,而林清玄的文字,恰逢其时。
到九十年代,情况有了变化,但追求宁静仍是一大趣味。因为,人们虽然远离了文革,却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感到眩晕。城乡巨变,消费升级,现代都市病的问题暴露在中国人的面前,工业革命后狄更斯、哈代、德莱塞、菲茨杰拉德津津乐道的问题,反而成为了中国作家眼中的新鲜事,焦虑成为都市人的习惯,于是,人们急切地想要求得缓解焦虑的灵药,让自己的生活体面、舒服的配方,这也是为什么,新千年后的部分城市人开始沉醉佛道,尽管他们未必真正懂佛学道术,但他们仍然乐于谈论《金刚经》《道德经》,在自己的社交网络感慨:“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林清玄32岁入山修行,35岁写成“身心安顿系列”,40岁完成“菩提系列”,创作“现代佛典系列”,他的人生和作品紧密结合,成为佛系清雅的最佳代言人。因之,即便跨越八零后、九零后乃至新千年的不同世代,林氏散文依然畅销不绝,丝毫没有凋零的迹象,而他散文中谈论的“随缘而生”、“缘起性空”,简而言之“放下”的哲学,也就成为一代人的标榜价值。
在去世之前,林清玄更新了一条微博,他说:“在穿过林间的时候,我觉得麻雀的死亡给我一些启示,我们虽然在尘网中生活,但永远不要失去想飞的心,不要忘记飞翔的姿势。”这是这位散文家给读者最后留下的体悟,而我想,思考“为什么失去想飞的心”这个问题,可能比不加反思地走向岁月静好更有意义。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