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菲“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 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 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 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 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 则素湍绿潭, 回清倒影, 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
也许因为有山有峡有大河,有宇宙感又有历史感,又可以顺江漫游,在文人骚客眼中,三峡不是远方,是诗的河床。
历代歌咏三峡的诗作超过4000首。《唐诗三百首》中,有30首写长江,有12首写三峡。诗人的名字,几乎串起了中国古代文豪录:屈原、宋玉、诸葛亮、郦道元、李煜、张九龄、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孟郊、刘禹锡、元稹、李贺、黄庭坚、王安石、司马光、苏洵、苏轼、苏辙、寇准、欧阳修、陆游、范成大、杨慎、王士桢、李调元等。他们有的曾在峡区为官作吏,有的曾在峡区旅居、漫游,共同点就是,留下了大量三峡诗篇。

中国诗歌史上最沉重、最深刻、最痛快、最雅致的名篇大部分也与三峡有关。屈原《九章》、《九歌》里大量的篇章讴歌了三峡的风土人情;宋玉的《神女赋》和《高塘赋》使“巫山云雨”变成了长江三峡的代名词;李白《早发白帝城》成为千古绝唱;白居易在三峡为官,写了200多首诗;曾在云阳和奉节白帝城旅居两载的杜甫,作诗437首,占到自己传世作品的一半。刘禹锡发掘当地民歌竹枝词,开一代新风,让竹枝词这种艺术形式走上文坛。李商隐的“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声情并茂。

可以说三峡每一段峡谷,每一片江面,无不平仄和谐。从雄壮的瞿塘峡,到婉约的巫峡,再到行云流水的西陵峡,三峡是段落分明而又酣畅淋漓的黄钟大吕。
据说奉节正在建一座“诗城博物馆”,还有张艺谋导演的情景诗词大剧《三峡归来》,让人们有机会永远记住历代名人与三峡的关系。
我宁愿称奉节为夔州,这样的一个地方应该配个特别有气质的词。一个地方,哪怕以物质形态早已地老天荒地存在着,但总是枯燥粗糙的。只有在经过文人墨客的描绘后,才变得具有精神性。

一处地名原本只是一个名词,当它经过古诗词的点化,这个地名就超越了名词的功能。你能看到它的走势趋向,是属于动词的;看到它的样貌色泽,是属于形容词的;而它引发的向往、赞叹、感伤,又抹上叹词的属性。
手捧《夔州诗三百首》,细细咀嚼这些被精心提纯过的语言,仿佛经历了千年雨露阳光的夔州,结出的一颗颗大地果实,自时间的深窖中,散发出浓郁的馨香。
夔州的风味是什么?还有什么比诗歌更有风味?吟咏千年也心甘情愿,心醉神迷?
无论是精短的绝句律诗,还是稍长些的乐府歌行,一代代美丽心灵的喜悦和伤悲,梦想与幻灭,或引吭高歌或低吟浅唱,流淌成一条情感与理智的江河水。
每一行诗句便是一条通道,让人得以穿越时光的漫漫长廊,进入彼时的天空和大地,道路和庭院,欣赏那里的四时风光,八方习俗。
因为这些诗句,一个原本抽象单调的地名夔州,有了色彩、声音和气息。
也许是遇上了中华大地最壮美的江山,走过夔州的诗人们,作品中体现的无论做事还是治学,眼界总是很宽,标准总是高定,更多的,是他们的悲欣交集。

余秋雨说,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
长江两岸,从古到今一直是不消停的疆场。白帝城也在文臣武将中变换着城头大王旗。清晨送走了李白们的轻舟,夜晚迎接刘备们的马蹄。
今天我们丰衣足食,难以回味那个辛苦的时代,他们漫游也好,隐居也好,总是很梦幻,像三峡云雨总有点漂浮。但他们的追求又是清醒的,所以《夔州诗三百》里,你看不到诗人们遮遮掩掩的朦胧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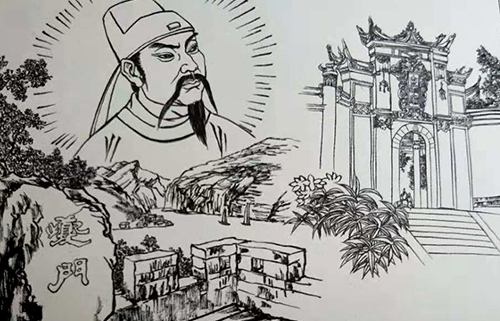
“那些诗人们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用一双慧眼、一腔诗情,在山水间周旋,与大地结亲。写出了一排排卖不出价钱的诗句。幸好他们很把做诗当正事,为之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摘自余秋雨《三峡》)
夔州最好的吹鼓手,当然推举李白了。一首《早发白帝城》,无论黄发还是垂髫,谁念不出谁就是文盲。李白是个多事好名者。在大唐盛世,倘若他没那么锋芒惹祸,温柔敦厚,也许他的人生就没什么烂摊子。

其实李白一生万重冰心在玉壶,与其他现实主义诗人的克制相比,李白总是剖心而出,就如《早发白帝城》的心理转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只要天子回心转意,遭贬一路的愤闷立刻抛入长江。我们脑补一下他的写作现场,李白用毛笔刷刷写下这些句子的轻歌慢狂就在眼前。李白其实没有走出儒家的边界,只是,他的玉质、明快、犀利,是会涤荡并拔高气场的,所以人们喜欢他。

诸葛亮的奉节“八阵图”,今人已经难以辨识,但这个虚无缥缈的“地图”,让无数文臣武将,写出了“一日看尽人生浮华”的诗。东晋名将桓温,永和二年伐蜀中,途径奉节写下了最早的提咏《八阵图》诗:“访古识其真,寻源爱往迹。恐君遗事节,聊下南山石”。唐代元稹写“气敌三人杰,交深一纸书......伤心死诸葛,忧道不忧余。”(《哭吕衡州六首》)。宋代王刚中写到“细思作者意,孔明有深策。高岸或为谷,滩石存遗迹。江海变桑田,平源犹可觅。故今两处存,千载必一得。”(《弥牟镇孔明八阵图》)

最经典的,莫过于杜甫的《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杜甫一生苦旅飘萍,偏偏在夔州,度过了短暂欢乐的稻农阶段,《茅堂检校收稻二首》写到:“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复新。谁云滑易饱。老借软俱匀。”
当然,杜甫在夔州留下的最著名诗篇,是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青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杜甫是个矛盾体,见到长江心胸扩大,见到夔州又忧苦凄怆。和他属于同一气质的,还有几百年后的文天祥。文天祥在夔州写了《读杜诗》:“平生踪迹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耳想杜鹃心事苦,眼看胡马泪痕多。千年夔峡有诗在,一夜耒江如酒何。黄土一丘随处是,故乡归骨任蹉跎。”

朝更代迭,诗人已去,诗一直活着。诗歌里的历史,不是镜子,是花开花落,朝花夕拾。故国、故城、故人芳华刹那。
不管怎样。夔州与三峡,接住了他们,荡去了浮华与浮生,留住了他们的精神晶体,至今熠熠生辉。
瞿塘峡,是三峡中最短的峡谷,山势雄峻,犹如斧劈,其中夔门山势尤为雄奇,是瞿塘峡的代表景观,也是长江三峡在景观上特征最明显的景观。古人诗称夔门为:“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

船行如人生,都是不可帆顺的,就像瞿塘峡的滟滪堆“不可下、不可上、不可流、不可触、不可窥、行舟绝”。
可以说,能留下千古传诵的诗人,都是有大局观的,正是因为他们站的太高看得太远,往往为当世之不容。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只能赴身清流,远谪他乡。
那个时代,最富庶的是中原与江南,西部南部都算偏远。文化精英们,很少是千里迢迢为旅游,去的原因基本一样贬谪或贬谪路过。
贬谪,是文官制度下的一种惩罚,被贬者不一定做坏事,被贬也不一定是坏事。他们贬谪的事功和著述,照亮了黯淡的岁月,也让履迹所至之处,原本生疏的地名,自此熠熠生光。

人们喜欢悲剧也害怕悲剧,我生性不喜读悲戚戚的诗,看到“出师未捷身先死”,赶紧翻过,“千里江陵一日还”,好,多读几遍。
牵连入永王谋逆案的李白,被流放到夜郎,路上走了一年,还没到目的地就遇赦,正好路过白帝城,这才有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早发白帝城》。这尽然是一首刚释放的囚徒写出来的诗。
顾况,在唐代诗人里是个典型的“大隐隐于市者”,并不想当多大的官儿,平日喝喝酒,写写诗,笑笑当朝权贵,结果屡屡被贬。他的诗风本就平稳流畅,到了夔州,立刻发现了土风土味的竹枝词的美。顾况是第一位以《竹枝词》为题写诗的人,“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荆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

还有个和顾况遭遇类似的窦常,也是个隐者。他在参拜夔州武侯庙时,感慨“人同过隙无留影,石在穷沙尚启行。归属降吴竟何事?为陵为谷共苍苍。”
广阔的宇宙间,人是多么渺小。阵石犹存,人事已非,蜀胜吴亡怎么样?联手抗曹又怎么样?到头来一片苍茫。
也许是瞿塘太险了,容易让人心生命运多舛的感慨。短命的李贺,27年的生命里,应该没受什么打击,也在瞿塘留下了戚戚艾艾的诗《蜀国弦》:“凉月生秋浦,玉沙淋淋光,谁家红泪客,不忍过瞿塘。”
思想与现实,精神与世俗总是难以弥合。名垂青史的诗人群体,拥有做事的智商,但这只是成功的一半;另外一半,则有赖于做人的情商。他们不愿意改变,不想要“摧眉折腰”的情商,所以总挨贬。

刘禹锡也有羁旅之仇,贬谪之恨,比如“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他参加王叔文永贞革新遭贬后,体察悟出抽象道理并具象化:“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但刘禹锡是个看透浮生的人,眼里的风景总是与众不同。他和王维一样,属于佛系诗人。王维视角描绘出的夔州瞿塘,就没有现实主义诗人的触景生悲、闻猿泪淋的感伤,而是“晴江一女浣,朝日众鸡鸣。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杪行。登高万井出,眺迥二流明。人作殊方语,莺为故国声。”(《晓行巴峡》)

所以今天的城里人,一定要到三峡去,才能阅读出古人的诗意,在城里最多阅读一个花园;到了三峡,阅读的是一个亘古洪荒,天地磅礴。
三峡是我国一种文体“竹枝词”的故乡。古书记载,武王伐纣时,南方少数民族有一支巴人的军队,他们一边战斗一边歌舞,这种表演形式到南北朝就演变成“竹枝词”。每逢节日,众多演唱群众手执竹枝,边歌边舞,庆祝丰收。

唐朝许多诗人都亲身观看过这种表演。杜甫和刘禹锡是开创竹枝新风的两位大家。杜甫在三峡期间,潜心研究这种民歌体裁,用这种文体创作自己的竹枝词。他所写的《夔州歌十绝句》,便是新的竹枝词的成功尝试,如“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白帝高为三峡镇,夔州险过百岸关”,通俗易懂、琅琅上口。
对竹枝词改造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刘禹锡。刘禹锡在夔州只有3年,但勤于采风,创作了竹枝体诗歌,为古代诗歌增加了一个新品种。著名的有《竹枝词九首》,吟咏夔州风土人情。
刘禹锡曾经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风云少年。33岁之前,刘禹锡一路青云直上,从监察御史做到农田水利部长。
然而,升得太快了,一旦下降,也会是加速度方向。唐顺宗即位,以王叔文为代表的一批人发动起政治革新运动。刘禹锡是核心人物,但革新如烟花,瞬间即逝。结局猜得到,刘禹锡、柳宗元等一同参与的八人遭贬远谪。

命运狠狠地给了刘禹锡一击,从朝廷的核心人物到贬谪的飘零人,内心要经历几多挣扎才能释然?
刘禹锡的一生,虽然不断地被排挤,被打击,被流放,但从没低头认输,反而是愈挫愈勇,豪情万千。他的豪情大雅气场强大,把民歌竹枝词的俗气也治好了。俚俗的竹枝词,从入的厨房,到上得厅堂。
竹枝词的原汁原味有点甜俗,比如写男女之情:“平生只有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到了刘禹锡的笔下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刘禹锡自己对夔州诗词改革也比较满意,“三年楚国巴城守,一去扬州扬子津。青帐联延喧驿步,白头俯伛到江滨。巫山暮色常含雨,峡水秋来不恐人。唯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别夔州官吏》)。作者自信他到夔州三年,竹枝词由俗变雅,会像《九歌》那样流传下来。
自古文人更多情,所以对谈情讲爱的《竹枝词》,骚客名流也总爱赋上一笔。比如白居易的《竹枝词其三》“巴东船舫上巴西,波面风声雨脚齐。”
王夫之,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也喜欢竹枝词并写的有滋有味“巫山不高瞿塘高,铁错不牢火杖牢。妾意似水水滴冻,郎心如月月生毛。”

从初唐到盛唐,由中唐到晚唐,一辈辈的诗句层层叠叠,仿佛三峡之颠上的白云青蔼,与山下的小城相望相映。
几百首夔州诗歌读下来,都能感到作者共同的一种心绪孤独。
孤独的同义词是出走。无论流放或旅行,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出走,从现实的群体、类别、规范里出走。
在入世的儒学传统中,文官们在辞官、失意、遭遇政治挫折走向山水的时候,一种心灵上的潇洒,尚没有办法成为一种完整的时代氛围。他们靠不断的出走,保持自己的理想。所以不难理解他们一到白帝城,总会伤古怀今。而且用语言通俗的“咏史诗”,凭吊刘诸。

奉节诗歌里“咏史诗”很多,比如胡曾的《白帝城》“蜀将一带向东倾,江上巍峨白帝城。自古山河归圣主,子阳虚与汉家争。”
今日社会,只要过了30岁,一个人关于社会公共与正义的理想,几乎就成了被嘲笑的词汇。但古人怎么有那么多,一生都在坚持理想呢?
有一直坚持理想最终成名的高适。高适一生创造了唐朝诗人两个唯一,一是官运亨通,步步高升至节度使;二是年过五十学写诗,不几年得大名,犹以边塞诗成名。高适也受打击,只是善于自我安慰,比如《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中,他写到:“嗟君此别意何如?驻马衔杯问谪居。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青枫江上秋帆远,白帝城边古木疏。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

但大多人学而优不能仕,人不达不能济天下,读万卷书用在何处?所以他们总是有着政治抱负不得释放的孤独。“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途径三峡时做《广溪峡》“庸才若刘禅,忠佐为心腹。设险犹可存,当无贾生哭”,抒发自己对国家兴亡的见解,即国家兴亡在德不在险,昏庸的君主即使有贤明的忠臣辅佐也扶不起江山。
连陈子昂这样的唐诗开篇压卷者,有着“念天地之悠悠”的宇宙观,在自我价值被现实生活无情地碾成碎片,沦落成一个心灵无所皈依的天涯倦客,站在三侠之巅,也会发出对生命的困顿。陈子昂对着白帝城和刘备永安宫,感慨到“古木生云际、孤帆出雾中,川途去无限,客思坐何穷”。

夔州的诗句就这样充当着时代的笺注,字里行间,有世相百态,有历史云烟,有心底沟壑,有眼前峰峦。王朝命运,人生遭际,相逢与别离,得意与失意。它们纠结缠绕,音律从高亢到凄凉,涵盖了宫商角徵羽,弥漫于东西南北中。

侠客,行万里路中将固有的规范变形,将平美如境的梦破碎重整。他们将在科举的教科书中学到的信仰,打碎或被动破碎,然后在行走中重建信仰。
看看唐朝隐逸诗人代表陆龟蒙的《峡客行》”万仞峰排千剑束,孤舟夜系峰头宿。蛮溪雪坏蜀江倾,滟滪朝来大如屋。”语言险怪,世事愤慨,大有侠客引刀一快的势头。
再看韦庄,一生辗转各地,60岁才熬到进士,但三峡美景抚慰了他,他看出了对立的美。“忆子啼猿绕树哀,雨随孤棹过阳台。波头未白人头白,瞥见春风滟滪堆”(《下峡》)。其他诗人都描写滟滪堆“奇、险、难”,他偏偏用春风比拟反衬。
皇室出生的纳兰性德,三千宠爱过一生,在评论诸葛亮护卫刘氏父子时,也有超越封建王朝的豪侠大气魄,比如《咏史》“劳苦西南事可哀,也知刘禅本庸才。永安遗命分明在,谁禁先生自取来?”

清朝虽兴文字狱,但总有几位气骨豪迈侠士。龚自珍看瞿塘“西来白浪打旌旗,万舶安危总未知。寄语瞿塘江上贾,收帆好趁顺风时。”(《己亥杂诗》)学者的积养、英雄的抱负、仙侠的气骨都在其中。
侠之大者,越大侠越孤独,越难以形容;如江河,越壮阔越难以描述。他们自滔滔滚滚,移向莽莽苍苍。
可能即使他们走出三峡,走到终点,也没有破译来世一遭的意义,可生命的意义,不就在于寻找意义的过程吗?
中国古画中大多是“山水行旅图”。画里画外,看见的是风景,看不见的是修行。

古代书院往往要选在山林,与现实社会保持距离。大自然显示的是宇宙的生命,即道的生命。在山林中读书,更容易体会到生命与天地之交流。诗人们是从古代书院里走出来的人,从小与自然亲近。他们的脚步,不像今天的新文化阶层,职位越高越匆匆。速度与深远是冲突的。古人没那么匆匆,他们脚步缓慢,就可以和自己对话,慢慢地储蓄和酝酿一种情感。想想那些诗人们,拥有独立高绝的思想和高妙的语言驾驭能力,是多么难得的事。他们因为独立的思想而精神富有,生命因此而灵动飞舞。
那些有着伟大思想的文学家、社会家、艺术家、政治家,无不是脚跟立定,眼睛却穿过滚滚云烟,眺望天地连接处。

读夔州里的诗人,总觉得他们没有衰老过,总是有着孩童的纯真和明朗,甚至老顽童的脾气与志趣,也许是因为三峡的水,诗人们泛起了百折不挠的韧性,更有了变通的灵性。他们表现出来的成熟,是心境如水,集包容,沉稳,渗透,涵盖,动静,取舍,进取等等智慧于一体。
由单纯到复杂,再回归成熟的单纯;由混沌到清醒,再回到清醒的混沌;由聪明到智慧,再回归到大智若愚。
所以我们看到了质朴又深邃的唐诗,还有质朴又深邃的古城夔州。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