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泥淖之子:现代诗歌从浪漫主义到先锋派》《记忆未来》后,广西人民出版社“大雅”子品牌“哈佛诺顿讲座”系列丛书日前新推出《别样的传统》。书中收录了美国著名诗人、纽约诗派领袖约翰·阿什伯利(John Ashbery,1927-2017)哈佛大学诺顿讲座的文稿。阿什伯利一生著有20多部诗集,几乎横扫欧美所有重要的诗歌奖项。向来言辞犀利的批评家布鲁姆·哈罗德不吝赞美:“当今英语诗坛,没有人能够像阿什伯利那样,以诗歌超越时间的沉重审判。”美国耶鲁大学英语系主任朗顿·海默教授评价:“没有哪位美国诗人的词汇量比他更丰富、更多样,惠特曼和庞德也不行”。
在《别样的传统》一书中,阿什伯利探索了自己极为看重的六位诗人的创作——约翰·克莱尔、托马斯·罗威·贝多斯、雷蒙德·鲁塞尔、约翰·惠尔赖特、劳拉·瑞丁和戴维·舒贝特,讲述了他们古怪而不为人知的生平。这些诗人声音强大、隐秘而狂野,他们沉浸在个人的痴迷和古怪理论中,这使得他们远离主流,而阿什伯利将他们视为自己“电池耗尽时诗歌的启动器”,他试图抓住每位诗人的奇异处,阐释他们留下的财富、尊严以及诗歌的真理,极大展现了他对诗歌创作的激情和洞察力。
因此,这本书也是通往阿什伯利那曲折、诙谐但晦涩的作品的一条捷径、一份邀请。经授权发布该书译后记,与读者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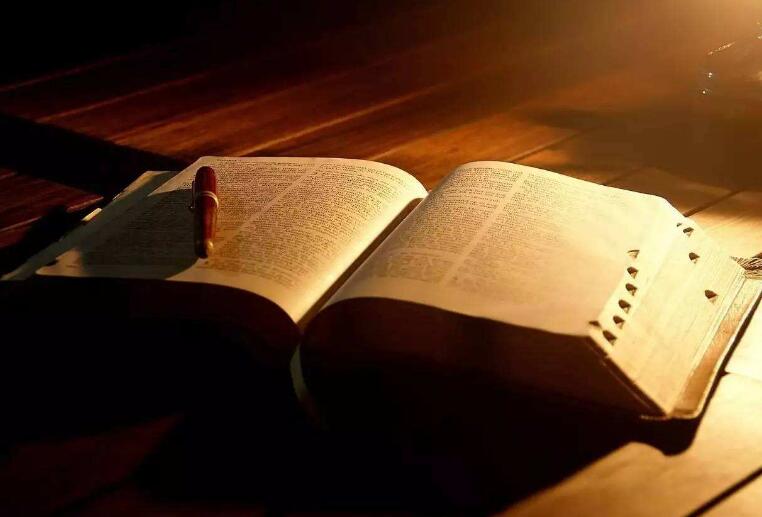
一种文化往往暗含着对另一种文化敞开的角度,这不一定是偏见,而仅仅是一种习性。基于一种文学传统对另一种文学的阅读难免是有局限的,而借助翻译的阅读则更可能有局限。局限当然也有其意义,能够昭示我们浸淫其间的文化如何限定我们向外看的视角,也暗含着我们即便打开自己的触角也还会是有选择的。从这样的角度看局限是为了反观自己。为了反观自己,更要从构成他者的历史具体性中获得充分的细节,因为只有对他者有丰富的理解,才有可能充实自己的反观。
文学译介,除了语言译转导致的差异甚至损失之外,作家作品的选择又会因为目的语文化的敞开角度而难免呈现出一种单线化或单面化的倾向。这种单线或单面往往还会显示为一种大师叙事式的文学史观或标准。
很有可能,我们把不同时代的所谓代表作家贯穿起来,形成某种进步的可理解的叙述,于是一种文学传统就以历时的文学史叙述构建并呈现出来,读者则依据选择性译介的作品再度构建一种外国文学史或文学传统,这样的阅读极有可能将一个时代的某位“大师”视为超越时代横空出世的强人。
譬如,对于美国诗歌,我们耳熟能详的是两个作为源头的大诗人:惠特曼和狄金森。然而,外国读者往往并不一定能将这两个诗人融入或还原到其文学传统中,或者说,译文中的他们没有所谓的传统或者原始语境,他们是超越时代语境和文化传统的作家。
我们阅读惠特曼和狄金森,似乎没有连贯性的传统,而是突然我们就读到了现代派,我们数出庞德、威廉姆斯,甚至和美国断不开联系的T. S. 艾略特、W. H. 奥登。
我们进而阅读一些更新的、日渐显赫的名字,例如我们阅读弗罗斯特、金斯堡、毕肖普、斯奈德等等,当然我们还阅读当代诗,见到这些诗人,就像我们来到一条河边,看到跳出来的鱼儿,我们说我们看到了河中的生命。
当然,我们可能无从看出那些不同的鱼儿从哪条支流而来,我们需要捉到一条鱼问问吗?
我是说,美国诗歌写作者如何化用其语言传统中内部资源、如何借鉴外部资源,除了学术性的研究之外,我们能否从写作者的角度了解呢?有必要吗?手头的这本书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条鱼。

这本书是美国诗人约翰·阿什伯利基于他哈佛大学诺顿系列的演讲改编而成的。他说他所讲的这六位诗人影响了他自己的写作,而这几位诗人又是我们的翻译所忽视的,事实上即便当代英语普通读者也忽视了他们,因此他不得不比较详细地讲述这六位诗人的生活与作品。
他们是约翰·克莱尔、托马斯·罗威·贝多斯、雷蒙德·鲁塞尔、约翰·惠尔赖特、劳拉·瑞丁和戴维·舒贝特(我故意不加上原文,估计很少有读者会想到在我们的译文中某处看到过这样的名字吧)。阿什伯利声称自己既非学者又非评论家,但他对六位诗人的评介却很充分,至于我们如何接受他的评介,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例如,我们在读后是否因此会寻找这些诗人的诗作来进一步阅读呢?我作为译者,在翻译之前和翻译过程中,确实阅读了这些诗人的很多作品。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