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狗年的脚步已近,天地间早已经流淌着春的气息,冰河正在一点点解冻,草木正在暗地里萌芽,人们正在敲锣打鼓地迎接春节的来临。大扫除的、备年货的、写春联的、贴年画的……忙忙碌碌,红红火火。春节确实是中国人心头最有分量的节日,我们在这个世辈相传的风俗节庆里,辞旧迎新,纳福迎祥,表达着对天地的敬畏,对亲情的倚重,对过去的感恩,对未来的希冀。
这么喜庆而热闹的节日,怎么能够少了图书的加盟呢?怎么能够没有读书的身影呢?不妨想一想,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进步与喜庆不正是内在自洽吗?读书又是取静之道,取静与热闹不正好互相补充、张弛有度吗?当然,读书说到底还是一件兴趣事,呼吁读书首先得推荐好书,于是就有了这个专版——由读书版的编辑们每人为读者推荐一本佳作,也借此机会感谢读者们的关注与支持。
近日读的书中,《孤独的行者》给我印象较深。这是一本散文集,作者陈启文近年把精力放在报告文学和人文随笔类散文的写作上。
学者乐黛云认为,散文应有“三真”之境,即真情真思真美。本书容纳了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叩问和反思,有研究者称是“在历史回望中探寻精神来路”,我比较喜欢其中把情景描述和历史记忆融合紧密的文章,如写扬州和瘦西湖的《境界》,写江南同里的《被时光收藏的小镇》及《楚辞里的江陵》等。
“瘦西湖美在自然,本色,而她的斑斓与丰富,则源于湖畔众多的园林。”写景是文章的重要部分,也是作者举重若轻的着墨之处。“这些园林之巧,不是巧夺天工,而巧在其因地制宜地借湖光山色来营造亭台楼阁,甚至不是营造,而是渲染,湖长十余里,犹如一幅山水画卷”。
更考验作者笔力的,是其把历史、人物融入景物描写之中,也显出作者的高明。“连阳光也显得出奇的宁静,视野格外的明亮与清晰,清晰得可以看见那艘从两百多年前徐徐驶近的一条画舫。船头,离水最近的地方,伫立着的可是乾隆弘历?”轻描淡写即把历史人物引入画中。如写僧人画家,“石涛来了。这个身如飘萍云游四方的苦瓜和尚,一来扬州,一见瘦西湖,就不想走了”;写难得糊涂的郑板桥“还有一个人,也时常会登上小金山,凭栏四望”“他因擅自开仓赈济饥民而获罪罢官,移居扬州后,本想靠卖画为生过几天清静日子,然而仍然难得清静,他眼前有太多的苦难和血泪,脑子又实在太清醒,即使把自己灌醉了,也还是难得糊涂”。
寄情山水之外,带有思考的精彩句子也时不时溜到读者眼前,“或许,醉与非醉之间,糊涂与难得糊涂之间,原本没有严格的界限,至少这个界限对郑板桥是不存在的”“在醉与不醉之间活着的,还有苏东坡”“我的脚步在这里慢下来,慢得可以听见时间的步履”,等等。
我之所以愿意读这样的文字,一个原因是,平时读到一些采风类的散文来稿,时常感到些许遗憾。或许是作者擅长搭建复杂结构却在描写烂漫景色,或许是作者观察不细,缺少思考,或许是作者时间紧迫,跑马观花,用流水账灌注文章,常感到欠缺些什么。而这本散文集中的文字,字里行间仿佛都有思考的痕迹,长文短句似乎都有情感的融入。作者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写作要有真诚的精神参与,要有深刻的生命体验。”我想,这是作者的追求,也是文字有价值的重要原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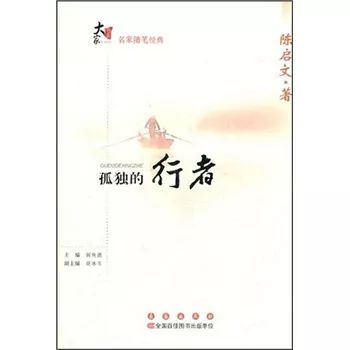
儿时,过年是和看戏连在一起的。如今,虽年味淡了,娱乐多了,但不少乡村仍延续着过年看戏的习俗,城市的舞台再炫,也有戏曲的一席之地。由此,想到重读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一书。
说它是专门研究中国戏曲发展史的开山之作,一点也不为过。《西厢记》《窦娥冤》《赵氏孤儿》,关汉卿、王实甫、白朴……今天的人们,对这些戏剧和作家,一点也不陌生。数百年来,这些戏、这些人其实一直很“红”,声名远播,粉丝无数,影响甚广。然而,正统学者对戏曲有偏见,正如傅斯年所说,“当时不以为文章正宗,后人不以为文学宏业”,探讨戏曲的学者寥寥可数,研究戏曲的学问乏善可陈。直到20世纪初,这部《宋元戏曲史》出现,“使乐剧成为专门之学”,才算是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用今天的眼光看,《宋元戏曲史》是一部真正的专著,学术价值毋庸置疑。但也正因为太“专”,对戏曲无感的人恐怕会望而却步。尤其是书中引用大量史料,罗列大批剧目,陈述众多作家,甚至用表格一一列举,翔实有余,生动不足,严谨有余,通俗不够。当今碎片化阅读时代,除了研究者,谁会乐意啃这样一个“冷骨头”呢?
其实不然。王国维的著作有其可亲、可读之处。在《人间词话》里,他用宋词名句表述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的三种境界,生动形象,诗情画意,妙趣横生,令人耳熟能详。除了大篇幅史料的铺陈,这部《宋元戏曲史》同样也有许多点睛之笔。翻开这部书,第一页《自序》就开宗明义,呈上一段“王氏经典”:“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类似的名言佳句在书中俯拾即是:“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
虽然是一部宋元戏曲史,但它更是一部断代中国文学史,其文学观、文化观、美学观至今仍给人以启迪;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与西方学术的逻辑推演紧密结合,其研究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30多年前,大学“古代戏曲概论”课上,老师曾隆重推荐这部书,并说:“看戏读史,相得益彰。”那时不太理解。现在感觉,读旧书如同老友交谈。像《宋元戏曲史》这部书,虽逾百岁,但老而弥醇,老而弥新,给人教益,引人深思。在过年之时、看戏之余读一读,也许别有一番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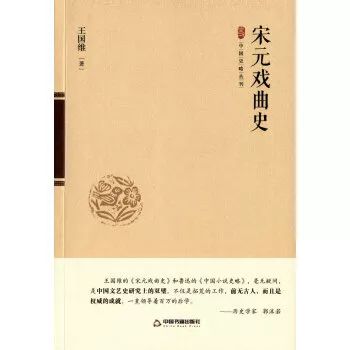
一根最不起眼的头发,能隐藏多少秘密?库尔特·斯坦恩的《头发:一部趣味人类史》,让我大开眼界。
从头发的进化史到各种毛发疾病,从理发师的起源到犯罪学的鉴证,从发型的政治表达到剃度的宗教含义,从头发艺术品的时尚风潮到乐器制造、环保领域甚至食品工业对毛发的妙用……在斯坦恩笔下,毛发变身为一座信息的宝库,装载了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勾画了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
斯坦恩曾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当了20多年教授,是毛发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正如书中前言所述,这次写作,源于他在理发店的一次经历。当理发师询问他的职业时,他回答自己研究毛发,理发师却说:“哦,别逗我了,先生!”斯坦恩由此感受到人们对毛发的狭隘观念,这促使他写一本书,阐述关于毛发的一切。
书中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毛发的生物学知识。动物体毛兼具保暖、防水、防晒、防蚊虫等一系列功能,人类的祖先为何放弃这套护身符,进化成“裸猿”?感到寒冷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汗毛倒竖?真的会“一夜白头”吗?秃头是怎么回事?等等。
二是头发的社会文化属性。头发传递着丰富的信息。发型有特殊的含义,古代社会,不同发型可能意味着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到了现代,一种特定的发型时尚往往可以代表一代人。许多文化都认为头发与灵魂有某种联系,民间故事中的巫术不少是以头发为灵媒,僧侣以剃度的方式表示放弃部分自我,日本相扑手在退役仪式上要剪掉头发,现代的印度女性也会把头发献给神庙……
三是毛发如何影响历史,以及它在当下与未来的各种用途。这一部分中,斯坦恩将视野扩展开去,介绍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几种动物毛发。古典时期,维京人靠皮毛贸易向东部和南部推进,最终打开君士坦丁堡的大门;海狸毛帽子的流行,使处理皮毛的工人大量出现汞中毒症状,成为英语中“疯帽匠”一词的由来;至于羊毛贸易对于欧洲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更是无需赘言。到了现代,毛发的“战场”已经变得极为广大,远远超出我们想象。
每部分都是图文并茂,有作者手绘的简单清晰的结构示意图,也有各处搜集的照片,可谓包罗万象。一滴水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小小毛发里,也蕴含着人类的全部历史。读完此书,你或许会对身边随处可见的寻常事物产生全新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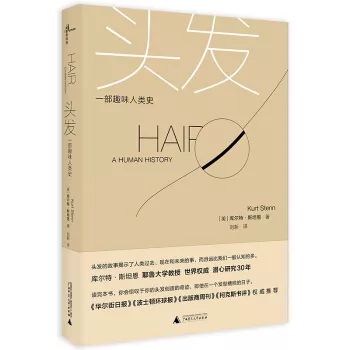
《头发:一部趣味人类史》:[美] 库尔特·斯坦恩著;刘新 译;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近几年,“诗词热”成为一种文化风尚,诗歌之美以更多元的视角被解读。当不同时代的读者对诗歌产生相通的情感投射与智识共鸣时,我们发现:这个时代不仅需要诗歌,更呼唤诗意和诗性的回归。但当诗歌已不再和日常生活发生直接关联时,我们应如何走近诗歌、诗人、诗心?诗歌如何被创造,又将带我们去往何处?这一连串关于“诗”的疑问,我在《诗的八堂课》中找到些许答案。
小32开、208页,我两天读完,酣畅淋漓。作者江弱水是浙江大学教授,这本书被学界称为“上乘的谈艺之作”,而作者自称是“一本关于诗的八卦”。我在书中也寻到“八卦”踪影,“此开讲第一回也,却说到赌博和下棋上头来了”,这是开篇第一句。以赌博和下棋为喻,讲李白是赌博型诗人,杜甫是弈棋型诗人,苏东坡手气好时不可思议,但也不经意会把牌打坏……
书以“课”为名,但读来从未让我产生距离感,行文方式也并非教科书式的循规蹈矩,而是具体可感、活泼而不拘泥。王国维、梁宗岱、朱光潜等近现代大家都曾试图用中国古典诗歌观念来理解西方诗学,比如,梁宗岱以中国古典诗学之“兴”来理解西方诗学之“象征”。江弱水做了同样尝试,他从诸如隐喻、意象、象征和境界等概念中抽离,重构以汉语古典诗学为核心的八课:博弈、滋味、声文、肌理、玄思、情色、乡愁、死亡。用抽丝剥茧的方式展开问题,探寻经典诗歌的内核生命力。
从莎士比亚到李商隐,从苏轼到鲁迅,从希尼到卞之琳……作者随手化用,即成文章。不拘中外、不限古今,落笔看似散淡,实则脉络清晰、环环相扣。在分属王羲之、杜甫、司汤达的诗句里,作者发现共同的“形而上学时刻”;在《诗经》《楚辞》《红楼梦》与莎士比亚、斯宾塞等人的作品中,作者发现相似的语言编码方式……这种串通古今中西的阐释打通了诗歌的壁垒,极具“诗学精神”,正如书中所言,“诗的精神是在世界黑夜中向着存在和语言的突围”。
很赞成江先生对诗歌的看法:“诗是招魂的声音,是宽纵和亲昵的音乐,是引领我们回家的路。”面对信息快速更迭之境,诗歌似乎进入“最坏的时代”,但在我看来,这也是诗歌最好的时代——大浪淘沙中必能涌现新时代的李白杜甫,忙碌喧嚣中诗歌必能带人们回归自我、诗意栖居。毕竟,“诗是一加一等于三也等于零的那种东西。当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诗就是看到的那个三、那个零”。

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是广而告之的一次徒步行走,出发前有人质疑,行进中随时有人加入,每天步行7个小时以上,15天行程近500公里。一年后就有了《从大都到上都》这本书。
忽必烈称汗后建立两都制,以今北京为大都,以开平,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为上都。这有点像游牧社会中的冬牧场和夏牧场。皇帝每年有大约1/4的时间是往返在大都与上都的路上。连接两都的道路共有4条,两条驿路是指由官方设置的用于人流、物流、信息流往来的重要通道,而辇路则专为皇帝南北巡幸而开。当年元朝皇帝仪仗浩浩荡荡,往来于南北之间,但留下的文字记载甚少,因此存在诸多争议。如今罗新要一个人走一走这条辇路。
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西方人一直对大都充满幻想,类似的旅行笔记层出不穷。600年后的山川草木有了不同的景致,一个写过小说、又接受过完整历史学训练的研究者的行走会有什么不同?在书中你会发现,罗新原来对所有的植物都很熟悉,不同的瓜果蔬菜,不同的小花,都能叫出名字。还有不同的鸟雀。比如他说他读到元代很多诗歌都记录上都附近有一种常见的鸟叫白翎雀。遗憾的是在路上已经看不到了。但这并不妨碍他借此展开历史枝蔓的梳理。史载成吉思汗与自己的结义哥哥扎木合本来亲如兄弟,但是后来两个人互相背叛,我们在后代的记载中看到了三个不同文本的记录。比如汉文的元史记载说,扎木合在王汗面前挑拨离间:“我于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鸿雁耳。”波斯文的材料翻译成汉语说,扎木合跑到王汗那里说,你看到了,我兄弟他走了,他不跟着我们,他就像雀儿一样(跑了)。而《蒙古秘史》讲这个故事时最为贴切: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儿,帖木真是散归的告天雀儿。两种雀儿,一种是白翎雀,一种是告天雀。罗新认为蒙古人对自己身边的那些鸟是最熟悉的,白翎雀的窝是比较稳定的,在一个树丛里面;而告天雀的窝是经常移动的。汉人写《元史》时,不知道告天雀为何物,擅自改成鸿雁。而波斯人在引用这个故事时,对这两种鸟都没有概念,所以只好就笼统地说成雀儿。通过这样的闲笔,罗新恰恰告诉了我们历史学家的美德。
罗新把他喜欢的行者安排在书中一一出场。比如在阿帕拉契亚步道上重新发现美国的比尔·布莱森,准备以7年时间重走“走出非洲”之路的“走出伊甸园”计划的实施者萨洛帕克。和他们旷日持久的行走相比,罗新的行走更接受社会的现实,他的书写也更充满忧伤。

现在,游记成了一种名声不太好的文体。原因在于,游记的写作门槛极低,作品数量极多,而精品佳作又相当反差地极难一见。我们读现在的游记,往往是一些行程的赘述、景点的介绍、历史的铺陈,以及空洞的抒情,这是游记作为一种特殊的散文文体,在成套路写作之后产生的最大弊病,它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散文“易作而难工”的古训。正因如此,在读到北岳文艺出版社的这本《贾平凹游记》后,我有了与读者朋友分享的念头。
贾平凹的游记颇带古风,有文人气,接续的是从公安三袁、竟陵派到张岱这一路晚明小品的文章传统,像《游寺耳记》等篇,简直就是从古人小品脱胎而来。
这些文章中,最精彩的是风景描写。有的是大段挥洒,有的则是随手的点画。他写水不扬波时的黄河,流动如“铜黄的牡丹在缓缓开绽”,写河里的旋涡,是“酒盅般大小地朝船头转来”,真是何其形象!他写雨后的山:“远处是铁青的,中间是黑灰的,近处是碧绿的,看得见的石头上,一身的苔衣,茸茸地发软发腻。漫天的鸟如撕碎的纸片般自由,一朵淡淡的云飘在山尖上空,数它安详。”层次分明,意境全出,形同水墨。这些是写实,《安西大漠风行》描写海市蜃楼,则是写虚:“果真那水越来越大,在地平线上连成一片,且开始出现一痕远山,有了孤岛,有了卧桥,有楼台林丛,有船,豆点人物。”这让人联想到张岱《湖心亭看雪》的名句:“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雅致不让前人。
真实的地理是写作的一个基本规律。中国地理尤其是地名,往往本身就是一种浓缩的文化,自带浓郁的文学气息,引之入文,不仅有虚实相间的效果,还常能增加文章的气势。是引地名入文的高手:“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到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指点江山,气势磅礴。贾平凹也深谙此道,他擅以地理之实写文学之虚。如《圌山》开篇便是:“八月为圌山来苏,先在江油一望,东北半空黛色,一山独立,只显得天低云白。江油古称孤城,孤城对孤山,山是好山,城也是好城。”寥寥几句,气势已是不俗。
贾平凹写景状物,不仅“道之独悉”,且常寓人世之慨。有时候,他之纪游,不写乐事,却写苦事,不写畅游,偏写苦游,尤为独特。他雨中登圌山,衣裤均被树枝剐破,“缩骨蹇背如雨中鸡”,拔腿一跑,却“一跤倒卧在那里”,可谓狼狈之至。他三赴华山,却耽于枯溪、小草与清潭,终究只是徘徊于山门之下。但他乐此不疲,并从中勘破人世的道理。贾平凹游记中殊多感慨,往往议论风生,见解独到,从中可看出他的积淀与才华。



发表评论